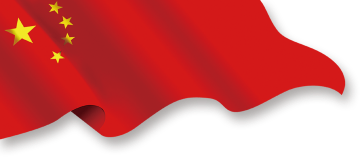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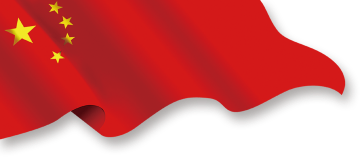
著名作家孙犁的小说《小胜儿》开头有这样一段话:“冀中有了个骑兵团。这是华北八路军的第一支骑兵,是新鲜队伍,立时成了部队的招牌幌子,不管什么军事检阅、纪念大会,头一项人们最爱看的,就是骑兵表演。”小说写于1950年1月19日。许多年里,我的心都被这支骑兵队伍吸引着。
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得知在1942年的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中,冀中军区骑兵团的白马连曾在河北蠡县南鲍墟村遭遇日军伏击,于是萌生了实地探访这一战斗场景、追寻白马连历史印记的想法。
“老人们都说,那就是白马队战士的墓。”老乡带着我从村里出来,指着村北潴龙河大堤外的土堆说。
我走近河堤仔细辨别,只见灌林、杂草掩着8座坟茔,从东至西规整排列。
老乡介绍说,“他们姓啥名谁,来自哪里,没人知道。只知道是骑着一色白马的八路军骑兵。”
“白马队?会不会是冀中军区骑兵团的白马连?”我下意识地问道。
据史料记载,当年冀中军区各部队除保留极少量骑兵用于通信,骑兵部(分)队全部集中到了骑兵团。1941年3月,骑兵团整编时,即按红马、黑马、白马编组战斗连队,白马连便是骑兵团4连。
回到北京后,我又查阅了不少资料,结合村里多位老人的讲述,终于还原了白马连在南鲍墟村战斗的过程。
骑兵团是冀中军区直接掌握的机动作战部队,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中,骑兵团执行“内线坚持”任务,以连为单位在根据地中心区不同地域活动。白马连由宋辅廷副团长率领,在肃宁、蠡县、博野一带活动,神出鬼没,频繁出击小股敌人,扰乱了日军“扫荡”部署。
1942年5月下旬的一个清晨,百余名白马连官兵从野陈佐村街上疾驰而过,朝南鲍墟村北河堤方向奔去,后面是一队紧追不舍的日军骑兵。蓦地,河堤上响起机枪声,多名白马连战士被击中,坠下马来。我前卫骑兵端起机枪还击,后续骑兵调转马身,挥舞大刀向着尾随的日军冲了上去。激战过后,白马连官兵沿河堤突围西去。突如其来的遭遇战使白马连遭到很大损失,队伍被冲散,牺牲了8位战士。
硝烟散去,老乡们在河堤附近发现了白马连战士和战马的遗体,场面极其惨烈。战士们衣服浸满血水,有的丢掉帽子,有的光着一只脚。一位烈士的口袋里装着一本被血浸染的“抗大”毕业证书,名字模糊不清。一名十七八岁的年轻战士背着牛皮包,里面装着几张文件、半张抹了酱的大饼和一把蔫掉的大葱。
南鲍墟村是抗日根据地模范区,群众对八路军感情深厚。战后当晚,根据地干部迅速组织群众开展烈士安葬工作。他们抬出了给老人准备的棺材、腾空装衣物的木箱,拿出白布、芦席……宋副团长也参加了安葬仪式。多年后,宋副团长在一篇文章中回忆,骑兵团团长马仁兴的长子马乘风,与其他7名烈士一起被埋在了潴龙河畔。如今,这7名战士的姓名已成了永久的谜。
白马连突围后,其中一支队伍闯过平汉铁路,到达冀中军区指挥所。宋副团长带着一支队伍随后赶到。两股人马会合后,重整旗鼓,杀回日军包围圈,继续坚持斗争。
6月上旬的一天,任丘城东南的一个小村里,宋副团长与骑兵团团长马仁兴相遇。得知白马连在南鲍墟村遭遇伏击和儿子马乘风牺牲的消息后,马团长面对地图沉默了两分钟。从不吸烟的他颤抖着点燃了一支香烟,招呼大家继续研究下步行动。宋副团长坚决要求带领白马连继续单独行动,于是马团长抽调30余人马补充至白马连,当夜他们即分开活动。不久,白马连在战斗中再次被冲散。
“牵着马儿回骑兵团”是冀中军区骑兵团失散指战员的心愿。孙犁在《小胜儿》中这样描写骑兵团战士小金子与部队失散后的心情:“他饭也吃不下,觉也睡不着。主任和那些马匹,马匹的东奔西散,同志们趴在道沟里战斗牺牲……老在他眼前转,使他坐立不安。黑间白日,他尖着耳朵听着,好像那里又有集合的号音,练兵的口令,主任的命令,马蹄的奔腾;过了一会儿又什么也听不见……”
队伍失散后,宋副团长带领仅有的几名战士着手开展收容工作,终于将白马连的一部分和兄弟部队失散的共200多名指战员带回晋察冀根据地。白马连另外40余人经过3个多月艰难跋涉,冲破日军重重阻挠,绕道回到晋察冀根据地。
在接下来的反“扫荡”斗争中,马团长曾带领部队多次从南鲍墟村附近经过,都没有机会看上一眼儿子的坟墓。
80多年过去了,白马连却从未远去,他们“艰难困苦而不溃散”的英勇事迹感动了全国人民。以冀中军区骑兵团为题材的电影《我和我的父辈·乘风》于2021年国庆节假期上映,在全国引起轰动。2022年,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修缮了冀中军区骑兵团白马连八烈士墓。
白马连的马蹄声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,但那些骑着白马冲锋的身影,却永远镌刻在了这片土地的记忆里。